荐书人 许志强
上世纪二十年代去巴黎流浪的文人艺术家,几乎都有一段贫穷落魄的经历。吃了上顿没下顿,千方百计拖欠房租,硬着头皮进当铺……像毕加索,穷到冬天烧画布取暖,简直是没辙了。相比之下,保罗·奥斯特的自传《穷途,墨路》(于是译),其描述的境况堪称优越。穷途也者,穷字当头,其物质性贫困首先就令人不堪承受。有人说毕加索穷归穷,还是要画画要做爱,但毕竟是饿着肚子画画做爱。这个方面乔治·奥威尔是深有体会的:说起在巴黎伦敦辗转流浪的故事,种种细节都离不开一个穷字。
他说一旦遭遇贫穷,就不得不掉入“谎言之网”。碰到卖烟的,问你为什么烟抽得少了,碰到洗衣妇,问你衣服是否送去别处洗了,你都支支吾吾讲不清。吃饭时间装作出门去餐馆用餐,其实是去公园看鸽子。反正整天要撒谎。去面包店买一个法郎一磅的面包,女店员切了不止一磅,而你口袋里只有一个法郎,想到有可能要多付两个苏,只好落荒而逃。街上遇见混得好的朋友,赶紧躲进咖啡店,而进咖啡店就得花钱,你用剩下的一点钱要一杯黑咖啡,里面却掉进一只死苍蝇。人一穷,倒霉的事也会多起来。等到每天连六法郎花销都难以保障,活着就纯粹是“难挨加无聊”了;因为填不饱肚子,在床上一躺就是半天。见到商店橱窗的丰盛食品,“一种几欲泪下的自悲、自怜感袭上心头”,想抓起一块面包就跑。有这种念头是很自然的,没这么做是因为胆小。要知道,连续一星期吃面包和人造黄油,人就不称其为人,“只是一个肚子,附带几件器官”,像波德莱尔诗中所说的“年轻的骷髅”,这便是贫穷赐予的东西。


(乔治·奥威尔 )
当时同在巴黎,海明威、亨利·米勒也都受穷,读一读《流动的盛宴》和《北回归线》便可得知。奥威尔的《巴黎伦敦落魄记》(孙仲旭译)揭示物质性贫困施加于生理和精神的作用,让人感到触目惊心。
落魄并不仅仅是指每天靠六法郎为生。对中产阶级知识分子来说,沦入底层而与穷人和粗人为伍,这才是更不堪的境地。说到这一点,奥威尔的独特之处便显示出来。他去巴黎是搞文学,期间写过两部小说,可他基本上不和作家、知识分子来往,而是混迹于乞丐、游民、妓女、酒鬼、劳工中间,与所谓的“被社会排斥者”为伍。虽说穷困潦倒是出于无奈,可他对物质境遇的改善确实也抱着无所谓的态度。他的生活方式是有些怪异的。一个审美的纨绔子弟,亦即具备良好艺术感觉的人,恐怕是只有在左拉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意义上才会接受那种辛酸龌龊的生存,而左拉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又何曾是像他那样,饿得比旅馆里的臭虫都不如。
奥威尔走投无路时在两家饭店做洗碗工,每天干十一或十四个小时,挣二十五个法郎。洗碗工是酒店里最低贱的工种,其秽恶让人不堪忍受,但总比躺在床上饿肚子好。落魄也有给人安慰的一面;“知道自己终于真正到了穷困潦倒的地步,会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几乎感到愉快”;“可以说身上越没钱,越是少担心,……你浑身上下只有一百法郎时,你会吓得魂不附体,等到你只有三法郎时,你就很是无所谓了。因为三法郎会让你直到明天还有吃的,你也不可能考虑明天以后的事”。
若非亲身体验,不会有此心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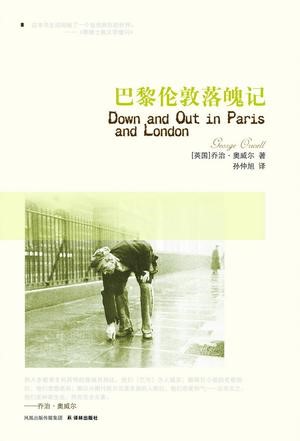

《巴黎伦敦落魄记》
作者: 乔治·奥威尔
《巴黎伦敦落魄记》揭开底层生活鲜为人知的一角,其形象和细节新颖,描述栩栩如生,写作上是很有原创性的。它的叙述相当有趣,甚至夹杂着巴洛克式的怪诞和幽默。阅读这本既让人发笑又让人忧伤的书,你会觉得奥威尔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作家!具象的画面,清澈冷静的短句,精准的细节……尤其是对贫穷和绝望的描绘,堪比挪威作家克努特·汉姆生的《饥饿》。
亨利·米勒认为,这是奥威尔写得最好的作品。
------【大家荐书】第2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