荐书人 牛浩江
1900年,当八国联军在北京烧杀抢掠时,一名远在德国的女子,谴责德国民主党没有组织抗议德国参加的联合武装。
她就是波兰、德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传奇人物,后来被称作嗜血罗莎、红色之鹰的罗莎·卢森堡(1871-1919)。《资本积累论》、《社会改良还是社会革命?》、《国民经济学入门》、《尤利乌斯小册子》等著作让她享有世界声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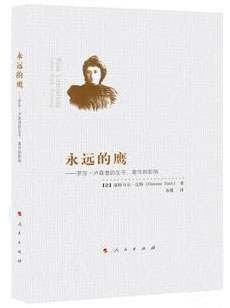

《永远的鹰—罗莎·卢森堡的生平、著作和影响》
作者:(德)迪特马尔·达特(Dietmar Dath) 著
金建 译
在当下,“主义”之争已无现实意义,全球共产主义阵营的歧异,未必比它跟资本主义的距离更近,我们要发现的是一个马克思主义忠实信徒之外的卢森堡。
这是一名对“普度迈耶橡胶园中可怜的牺牲者和把躯体献给欧洲人当球玩的非洲黑人”抱着亲近之心的女性。“我觉得在整个世界上,凡是有云彩、有飞禽、有人的泪痕的地方,都如同在家乡一样。”按照常理,这样细腻感性的内心无论如何不会与一个坚定的女革命家联系在一起,然而,两者确实在卢森堡身上重合了。
.gif)

图片来源于网络
德国思想家汉娜·阿伦特的笔有着最真实的罗莎:“而罗莎,用她半开玩笑的自我评语来说,天生就是个‘书呆子’,假如不是世界状况冒犯了她的正义和自由感的话,她完全可以埋头于植物学、动物学、历史学、经济学和数学之中。”可以揣测的是,在当时的情形下,共产主义是最接近她的理想的理论,符合她永远站在弱势一方的天性。
在中国历史上,这样的身份错位也许能在诗人皇帝李煜、木匠皇帝朱由校身上找到影子,但不同的是后者的原因在于先天身份,而罗莎·卢森堡却是源于主动。这颗投身运动的种子早已埋下,1885年,中学生罗莎·卢森堡赠给女同学照片背面的题词是:“能够以纯洁的良心去爱所有的人那样一种社会制度,是我的理想。”
.gif)

图片来源于网络
不幸的是,完美施于艺术是更好的艺术,施于社会构建则往往是灾难。命运开了个玩笑,让她在社会事业中扮演了一个不合时宜的角色,在个人领域也没有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
到20世纪初,罗莎·卢森堡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地位已经举足轻重,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在报章和集会中的核心人物,在1900年7月17日的一封信中写道:“(艺术)近来强烈地吸引着我……紧张的工作之余,我就阅读艺术史,参观美术馆和观赏歌剧。”
紧张的政治斗争似乎耗尽了罗莎的全部精力,但是却没有妨碍她专心致力于植物学的研究。她在1915年回忆道:“我对植物产生了强烈的爱好,我开始采集植物,把它们晒干并收集起来……现在,我有十二个装满植物标本的纸夹子……”
1916年2月,罗莎·卢森堡再次被捕入狱后“甚至还在小花园里开辟了两个花坛,她的书箱也运来了”。
副本.gif)

图片来源于网络
在1917年,罗莎·卢森堡在通信中写道:“战争结束后,你知道我们将要做什么吗?我们一起到南方旅行去……你想象一下:广阔、雄伟的景色,到处是山岭和峡谷的俊俏棱角,上面是一片灰沉沉的光秃岩石,下面是葱茏茂密的橄榄树……”
1919年1月15日晚,罗莎·卢森堡被资产阶级“自卫兵团”逮捕,枪杀,用铁丝缠上尸体,扔进了科尔涅利乌斯布留克附近的兰德维尔运河。
本来,这个世界上可以多一个女艺术家、植物学家……


图片来源于网络
------【大家荐书】第50期